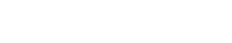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副教授仇凤仙解释,在学术界,上世纪70年代及以前出生,并于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间外出务工的农民人群,被称为“第一代农民工”。
2015年,“高龄农民工”话题屡屡被学界及媒体讨论,出生在安徽北部农村的仇凤仙也开始留心调研。此后数年间,她向全国多省份的第一代农民工发放2500份调查问卷,并与200余名第一代农民工展开访谈。调研内容集合成册,2023年6月,她的新作《第一代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研究》即将出版。她希望为第一代农民工群体“画像”,也希望以此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视角。

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副教授仇凤仙。受访者供图
有活儿干就是幸福
新京报:你开展关于第一代农民工的调查研究,源于什么样的契机?
仇凤仙:大概在2015年左右,“高龄农民工”这个话题开始出现在媒体上。我回老家时,也会碰到一些常年外出打工的亲戚、邻居,他们看我在大学任教,就都来和我讨论,以后年纪大了,不能打工了,要怎么办?
他们当时都在五十岁左右,大部分人在工地上干活,看到许多工地已经不收六十岁以上的工人了,都开始担心自己未来的生计。那阶段的讨论启发了我,我从2016年开始,就有意识地做这方面的调研了。
经过后来的几年调研,我发现第一代农民工普遍在五十到七十岁之间,他们多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外出务工了。他们务工最主要的驱动力,就是“生计驱动”,希望改善彼时家庭窘迫的经济状态。这在过去的农村是最普遍的情况。我也是皖北农村人,如果我当年没有考上高中和大学,我肯定也早早出去打工了。
新京报:你是如何与这些受访者产生链接的?
仇凤仙:开始正式调研后,每到寒暑假,我都让我的研究生们各带几百份调查问卷回老家的村里。我们学校有不少学生的家人都是在外务工人员,我有时也会托他们填写问卷。这些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反馈来的样本范围也比较广。
我自己常去全国各地出差、开会,也会带一沓问卷在行李箱里。在不同城市的路上、小饭店或者小区绿化带碰到高龄农民工们,就试着让他们填一下,或者直接与他们聊聊天。最终,我们共发放了2500份调查问卷,与超过200名农民工进行访谈。
新京报:第一代农民工主要从事哪些工种?
仇凤仙:在我的调研中,有43.4%是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在餐厅打工或者做类似后勤工作的,占比10.5%;做保安的占比6.5%;还有40%是个体户、自雇佣或者在工厂打工。
我觉得,在城市里要找到第一代农民工还是挺容易的。往往就是上了年纪的,做保洁、保安等工作的,要不就是在建筑工地的。
和第一代农民工一同起步的,是我国社会建设最高速发展的时期,那时候建筑工地对农民工的需求量大,门槛低,对他们而言是很不错的选择。和新生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无论是学历还是专业技能都比较欠缺,他们进城后唯一可以交换的就是力气。
新京报:你曾经提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第一代农民工虽在城市里从事低水平、低收入的工作,但彼时他们的收入仍远高于在农村种地的收益。近些年来,这种差距还明显吗?
仇凤仙:这是必然的,农村的挣钱机会依然是远远少于城市的。我可以给你简单算一算,比方说,北方农村每年种一波小麦,种一波黄豆。小麦价格在每斤一块多点,一亩地能收1000斤,黄豆是每斤三四块,一亩地能收三四百斤。也就是说,一亩地,一年的总收入也就三四千元。即使有人家里的地多一些,总收入也不会太高。
但是农民工哪怕是做日结工作,比如在城里干保洁,一天也能挣至少八九十元,一个月就有两千多。60岁以下的农民工,还能在建筑工地干活儿,一天能挣300元左右。工地的活儿看天气也看项目,有些受访的农民工会和我说,如果天天有活干,那他们简直太幸福了。
“代际跨越”的成与败
新京报:你多次提到,第一代农民工身上背负着“代际跨越”的使命,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仇凤仙:我的许多调研对象都和我说,最早出去打工,就是想挣点钱给家里花,改善下条件,别的没想太多。但是在城里呆久了,见到不同的生活方式,发现城里年轻人有许多的发展可能,就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上大学,不再走自己的路,不再做农民工——对于他们来说,成功的“代际跨越”有两个标准,要么孩子考上了大学,要么孩子能够拥有体制内、大企业等比较稳定、体面的工作岗位,并且最终可以在城市里扎下根来。
在我的实际调研中,第一代农民工的后代考上大学的,可能占比20%左右。进入体制或大企业的更少,占比5.1%左右。大部分第一代农民工的后代,仍继续出去打工。真正能在打工城市买房安家的少,大部分后代只能够在自己家乡附近的县城买房子。
不过,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这几年回村都开上了小轿车。第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后,回来比谁家的房子盖得好。他们的孩子外出打工后,回来比谁家的车更高档。所以说,虽然都是农民工,但新生代农民工的物质生活水平是明显高于父辈的。
新京报:同样是进城务工,第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方向有变化吗?
仇凤仙:新生代农民工去建筑工地的不多。前几天我访谈的一个包工头就和我说,虽然工资一天能开两三百,但年轻人都不愿意去工地,太苦了。他们情愿去中高端的餐厅做服务员,因为那里有发展空间,可以从普通服务员做到领班,做到店长。
我曾访谈过一个三十多岁的女性农民工。她说自己16岁就外出打工,最早在南方的一个纺织厂流水线上工作。后来自己开卤菜店、给宴会扎气球、在花店学插花等等,可以说用尽了一切机会去学手艺。
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强烈的自我意识,你问他们为什么要出去打工,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想去见世面,想获得自我发展,想摆脱农村的生活方式等等。但是对于他们的父亲母亲来说,外出务工最大的驱动力就是挣钱、改善家境。他们没有多的想法。
新京报:在城市融入度上,第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有差异?
仇凤仙:在这方面,新生代也比父辈的融入程度高。我访谈过一个六十多岁的农民工,做保洁的,进城务工有三四十年了。他说他几乎从来不去商场、公园,他的生活就是两点一线,宿舍和工作地。有些受访者会和我说,自己说方言,和城里人交流会觉得不自在。
总的来说,我调研的第一代农民工,对于城市的归属感是很低的。但他们的后代,也就是新生代农民工是自信的。他们会很兴奋地说自己曾经在哪个城市工作过,感觉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座城市的一员。他们在下班后也会去逛商场,进行一些城市消费。事实上,今天走在街上,你已经很难区分面前的年轻人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了。
当然,新生代农民工也有进城的适应期,比方说,杀马特文化就是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出来的,是他们中的部分人对走向城市文化的一次尝试。

仇凤仙与小区做绿化带保洁的农民工交谈。受访者供图
权益被侵害,要有自我保护意识
新京报:你曾提到,第一代农民工在劳动权益遭受侵害的时候,求助渠道往往是亲戚朋友,而非寻求劳动保障或者说公检法机关的帮助。
仇凤仙:有关调查显示,当第一代农民工的权益遭受不法侵害时,例如被拖欠工资、遭遇工伤事故等等,有41%未得到有效解决,还有13.5%的人并未求助。
权益侵害中,最典型的就是拖欠工资。这些年我做访谈,听他们说得最多的就是外出务工担心被骗,担心白干活。很多时候,他们进工地、找活干都是熟人介绍,被骗了就自认倒霉,没有“找公家”的意识。
其实,在我的观察中,这几年拖欠工资等对劳动权益的侵害已经少了很多了。这和我们国家的大环境有关。2000年以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专项政策,包括为农民工尽可能地开展就业机会,为农民工建立工伤保险,以及出台专项清欠活动等等。国务院每年年底都会有一个专项活动来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如果企业撞上这个枪口,是会被罚得很严重的。
另外,从2015年左右开始,国家施行同舟计划,让工伤保险固定工地,不固定人。只要在这个工地上发生事故,工人都可以走工伤保险报销。这样一来,流动性比较大的农民工也能正常参加工伤保险。
可以说,很多政策本身是很有作用的,但是许多尤其是高龄的农民工,他们对这些政策没有概念,也不了解。而且,对于他们而言,找公检法,打官司,都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这么做的。他们会告诉我,觉得进法院是一件“恐怖的事”。像费孝通先生说的,哪一家要去打官司,他们在传统社会是不受待见的。
新京报:如何纾解这样的局面?
仇凤仙:首先,地方上的劳动管理部门,可以开展一些活动,用一些案例去激发起第一代农民工的自我保护意识。我们高校的学生和志愿者,也可以去地方上宣讲,对农民工进行一些科普活动。
最好的办法,还是公益的法律机构要发挥作用,在第一代农民工遇到问题、有需求时,能及时的告诉他们该怎么做。比如说,可以在建筑工地里面,在一些务工市场,张贴科普海报:你遇到这些权益被侵害的问题该怎么处理?再留下求助电话等信息,方便有需求的农民工来联系。
回乡养老目前还是唯一的选择
新京报:在享受社会养老保险方面,第一代农民工群体的现状如何?
仇凤仙:第一代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主要有两条路径,加入城镇的职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和参加农村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保的门槛较低,但是它的待遇也低,基本都在300元每月以下,很难满足农民工将来的生存保障。
在我的调研中,第一代农民工参加农保的参保率是65%,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率只有5.9%,自己购买商业保险的是2.9%,没有参与任何社会保险的占比26.2%。
这里面有很多现实因素。首先,农民工要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必须签订劳动合同,但是我调研发现,签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只有百分之三十。另外,农民工的流动性太高了,一旦跨省打工,就要面临养老保险续接的问题——他只能带走他个人账户里的费用,可能只占总缴存的3%。所以很多农民工对缴养老保险很不积极。
这类高流动性、跨省带来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妥善的解决办法。从现实角度来说,解决起来也比较困难,它需要被提高到国家层次来统筹,但是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很难办。
新京报:面对工地清退高龄农民工的现状,第一代农民工是怎么应对的?
仇凤仙:他们没有太多的特殊应对。建筑工地进不去了,就退而求其次,去日结市场,到小区做保安或保洁。做这些工作,福利保险当然是没有的,干一天活,拿一天工资就回去了。
在有些建筑工地,还是会有60岁以上的农民工在干活。我国工伤保险的截止年龄是60周岁,所以这批超龄建筑工也是没有任何保险的。
即使这样,愿意去工地的超龄老人还是很多。建筑工地一天挣三百元,日结市场一天挣一百元左右,回村里务农,挣得更少。而一位身体健康的农村老人,在65岁以前继续在工地干活,从体力的角度来说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其实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想去挣钱更多的地方。
前不久,江苏省住建厅发布了有关试点通知,要求对超龄建筑工人数量设定比例上限。这是不再“一刀切”限制超龄农民工进入工地的信号。

2023 年2 月3日,北京通州马驹桥劳务市场,招聘启事上都明确显示不招大龄打工者。 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新京报:第一代农民工对未来养老的期待是什么样的?
仇凤仙:我的受访对象们都说,没有什么养老的打算,干到干不动了,生病了,就不干了。他们不会预设退休年龄,背井离乡出来这么多年,前几十年都在供养家庭,等到60岁以后,子女往往也到中年了,孙辈都长大了,他们就要给自己攒养老钱了。
我认识的最高龄的农民工有七十多岁了,还在做打扫卫生的护工,离家很远。但是做护工包吃住,月工资也有四千多元。我调研的第一代农民工中,家庭存款在3万以下的,占比41.3%。他们至少要攒够养老钱才回乡养老。
新京报:回乡养老是唯一的选择吗?
仇凤仙:普遍来说是的。他们自己没有多余的经济能力在城市安家。国内现在有一个“晋江模式”——通过放开户籍限制、探索居住证制度等方式,让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享受到市民化待遇。你给农民工提供了充分的社会福利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后,回乡养老可能就不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了。
当然,如果在家乡就有保障,或者有好的工作机会,不少大龄的农民工肯定也愿意回家。这取决于我们能否立足于乡村去解决他们的问题,能否由各地政府根据自己的地方特色,因地制宜地去发展特色项目、特色产业,向高龄农民工提供就业机会。
比如说,在未来,我们能否通过政策,吸引更多的工厂建造在乡村?让农民工在家门口就可以进厂打工。政府和社会组织有没有可能在乡村开辟一些公益性的岗位?我认为,从政府、资本、社会组织的角度,都可以在乡村为农民工创造就业的方式。多管齐下,为超龄农民工再搭建10年左右的生计资源,等他们从60岁干到70岁,攒够养老钱了,他们可能就不干了。
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不一样,他们从来没有脱离乡村,他们在外务工几十年,往往都是农忙时回村,农闲时外出打工,像候鸟一样飞来飞去的。所以,如果在家门口就能有适合的岗位,那他们也愿意和乡村和土地去重新建立长期的联系,继续发挥他们的余热。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编辑 胡杰 校对 李立军